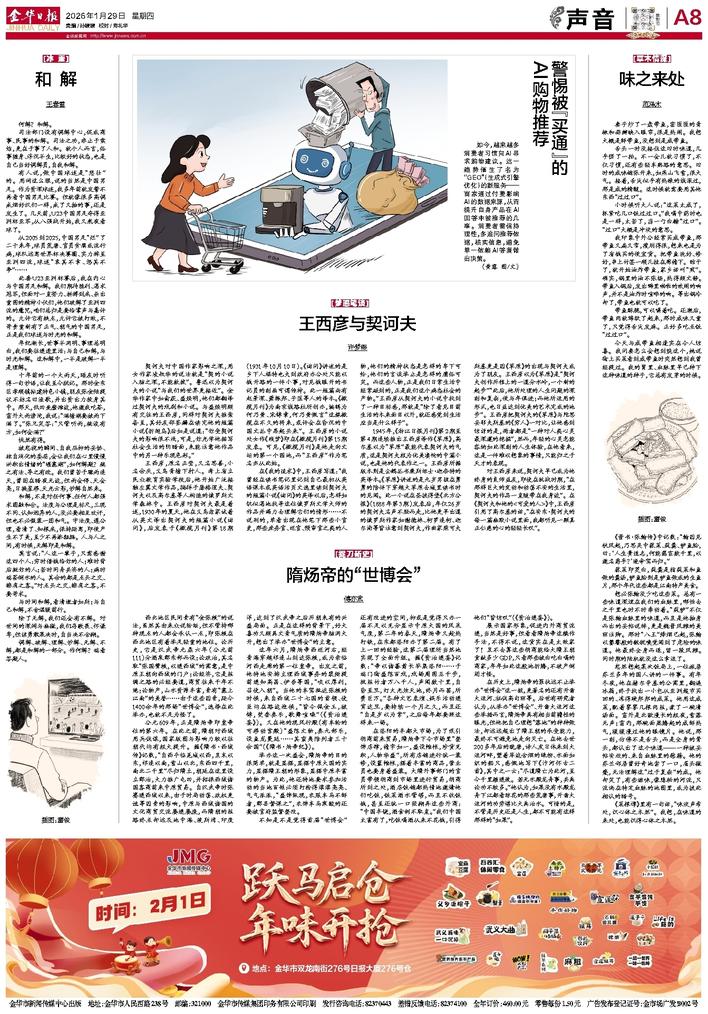[草木情深]
味之来处
范泽木
妻子炒了一盘带鱼,密匝匝的青椒和蒜瓣映入眼帘,很是热闹。我想大概是鲜带鱼,没想到是咸带鱼。
舌头一时没接住这旧时味道,几乎愣了一拍。不一会儿就习惯了,不仅习惯,还有些轻车熟路的意思。旧时的咸味铺张开来,如燕山飞雪,很大气。接着,舌尖似乎有热辣的线滚过,那是咸的精髓。这时候就需要用其他东西“过过口”。
小时候听大人说:“这菜太咸了,抓紧吃几口饭过过口。”我喝中药时也是一样,太苦了,舀一勺白糖“过口”。“过口”大概是冲淡的意思。
我印象中外公经常买咸带鱼,那带鱼又扁又窄,瘦削得很,想来也是为了省钱买的便宜货。把带鱼洗好、修好,串上竹签一顺儿挂在廊檐下。晾干了,就开始油炸带鱼,家乡话叫“煎”。确实,锅里的油不张扬,热得颇文静。带鱼入锅后,发出噼里啪啦的欢闹的响声,并不是油炸时喧哗的响。等出锅冷却了,带鱼也就可以吃了。
带鱼酥脆,可以嚼着吃。还潮后,带鱼肉就绵软了起来,那时咸味又重了,只觉得舌尖发麻。正好多吃点饭“过过口”。
今天与咸带鱼相逢实在令人惊喜。我问妻怎么会想到烧这个,她说街上买菜看到咸带鱼时突然想到我曾经提过。我的胃里、血脉里早已种下这种味道的种子,它总有发芽的时候。
《晋书·张翰传》中记载:“翰因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,曰:‘人生贵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,以邀名爵乎?’遂命驾而归。”
菰菜即茭白,莼羹是指莼菜和鱼做的羹汤,鲈鱼脍则是鲈鱼做成的生鱼片,那个年代这些都是江南特产美食。
想必张翰没少吃这些菜。总有一些味道深埋在我们的血脉里,哪怕去之千里也时不时牵动着。“莼鲈”不仅是张翰血脉里的味道,而且是他抽身而出的妥帖说辞,更是魏晋风雅的美丽注脚。那时“八王”烽烟已起,张翰以饕餮般的敏锐嗅觉闻到了危险的味道。他最终全身而退,留一段风雅。同时期的陆机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忽然想起某次饭局上,一位旅居芬兰多年的国人讲的一件事。有年冬夜,他在赫尔辛基的公寓里,翻遍冰箱,终于找出一小包从亚洲超市买回的、冻得硬邦邦的咸菜。他用这咸菜,配着寥寥几根肉丝,煮了一碗清汤面。窗外是北欧漫长的极夜,雪落无声;窗内,那碗面蒸腾起的咸鲜热气,缓缓漫过他的眼镜片。他说,那一刻,仿佛不是舌头,而是全身的骨头,都认出了这个味道——一种被妥帖安放的、来自血脉里的慰藉。他的芬兰邻居曾好奇地尝了一口,眉头微蹙,无法理解这“过于复杂”的咸。他却笑了,有些滋味,像隐秘的河流,只流淌在特定血脉的地图里,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。
《菜根谭》里有一句话,“味淡声希处,识心体之本然”。我想,在味道的来处,也能识得心体之本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