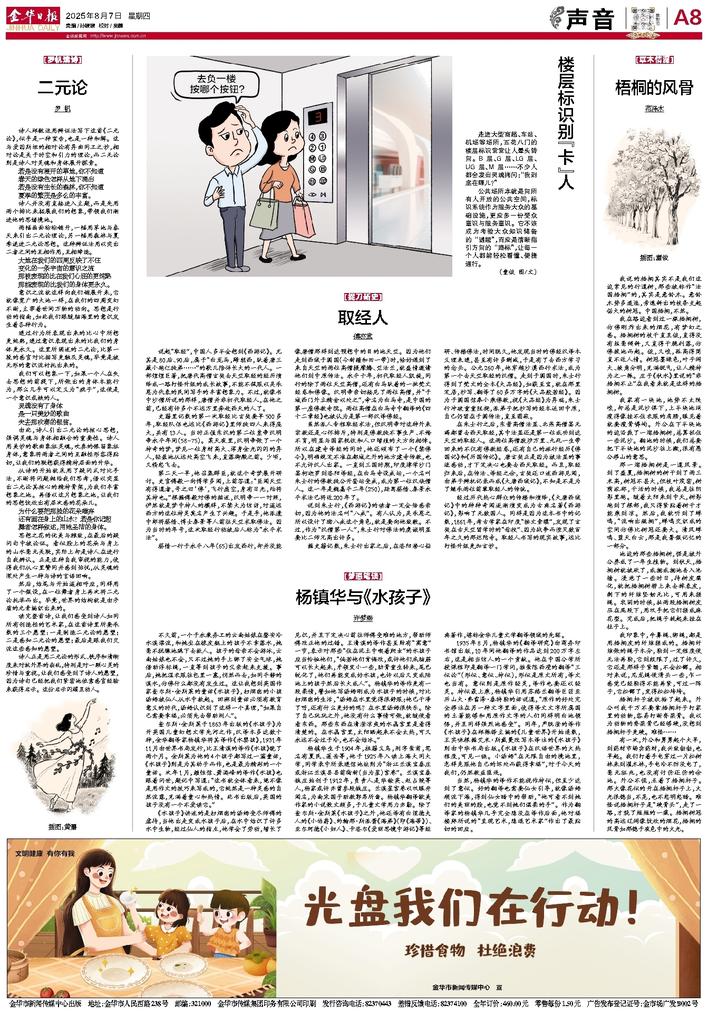[草木情深]
梧桐的风骨
范泽木
我说的梧桐其实不是我们这边常见的行道树,那些被称作“法国梧桐”的,其实是悬铃木。悬铃木势多逶迤,旁逸斜出的枝条支起偌大的树冠。中国梧桐,不然。
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棵梧桐树,仿佛刚炸出来的烟花,有梦幻之感。梧桐树的枝干直且俊,直得没有丝毫倾斜,又直得干脆利落,仿佛拔地而起。俊,又峻,孤高得简直不近人情。树冠墨绿色,叶子阔大、棱角分明,充满锐气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庄子《秋水》里说的“非梧桐不止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梧桐树。
我家有一块地,地势不太陡峻,却总是泥沙俱下,上半块地消瘦得像挂不住衣服的肩膀,眼见着就要瘦骨嶙峋。外公在下半块地的边沿栽了一溜梧桐树,总算拦住一些泥沙。翻地的时候,我们总要把下半块地的泥沙往上搬,很有愚公移山的意思。
那一溜梧桐树是一道风景。到了盛夏,梧桐树的树干到了两三米高,树冠不甚大,但枝叶茂密,树荫浓郁,干活的时候,我总是往阴影里跑。随着太阳来到中天,树影跑到了根部,我只得紧贴着树干才能乘到凉。然后,我就听到了蝉鸣,“流响出疏桐”,蝉鸣交织成的空间仿佛比树冠还要大。清风蝉鸣、蓝天白云,那是我暑假记忆的一部分。
地边的那些梧桐树,愣是被外公养成了一年生植物。到秋天,梧桐树就被砍了,成捆成捆地丢入池塘。浸泡了一些时日,待树皮腐化,就把梧桐树捞上来去掉表皮,剩下的纤维坚韧无比,可用来搓绳。农闲的时候,扯两股梧桐树皮压在屁股下,用双手把它们搓成麻花型。完成后,把绳子拢起来挂在柱子上。
我印象中,牛鼻绳、绑绳,都是用梧桐皮的纤维搓成的。梧桐纤维做的绳子本分,勒到一定程度便无法再勒,它到极限了,过了许久,它还是那样子紧绷,不会松懈。相对来说,尼龙绳便滑头一些,乍一感觉已经勒得不能再紧,可过一阵子,它松懈了,变得松松垮垮。
梧桐杆子被收拾了起来。外公叫我千万不要拿梧桐杆子打家里的动物,容易打断脊梁骨。我以为动物的脊梁骨已经够硬,没想到梧桐杆子更硬。难怪……
有一次,外公和舅舅起个大早,到药材市场卖药材,我兴致勃勃,也早起。我们打着手电穿过一片松树林来到灌木林,手电冷不防没电了,毫无征兆,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外公不慌,点着了梧桐杆子。那火像花似的开在梧桐杆子上,火光很稳当,不晃,也不忽明忽暗。难怪说梧桐杆子是“硬骨头”,走了一路,才烧了短短的一截。梧桐树冠的高远辽阔像绽放的烟花,梧桐的风骨如那稳于夜色中的火光。